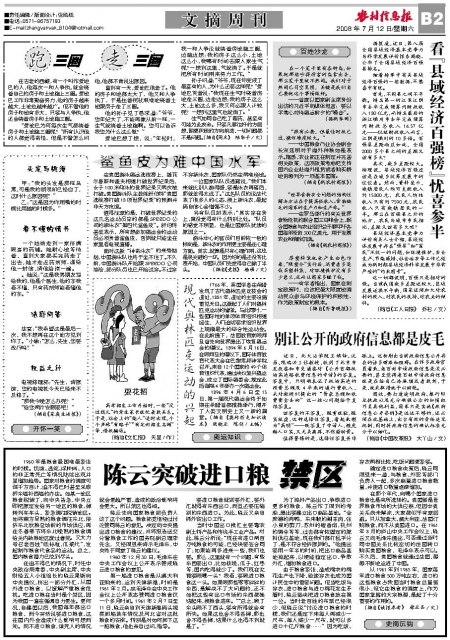陈云突破进口粮禁区
1960年是粮食最困难最紧张的时候。饥饿、逃荒、浮肿病、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等情况陆续出现并呈增加趋势。国家对粮食的调度可谓千方百计,迫不得已时甚至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如某一地区粮食脱销了,向中央告急,中央立即把原定发给另一地区的粮食,掉转列车车头,紧急调往脱销地区。如将南方早熟的粮食调往东北,接济东北秋粮登场前的市场供应,再在冬春季节将东北晚熟的粮食调给关内缺粮地区度过春荒。又大力号召老百姓“低标准,瓜菜代”,发起制作粮食代食品的运动。总之,国内粮食潜力已挖到尽头。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财经五人小组组长的陈云果断向中央提议,挤出一部分外汇,从国外进口粮食,以缓解严重粮食危机。吃进口粮在当时是个禁区,因为我国一直在强调自力更生。更何况,自建国以后,我国每年都出口粮食,而今突然说要进口粮食,这在国内外会造成什么影响可想而知。而不进口粮食,饿死人的情况就会更趋严重,造成的政治影响将会更大。所以禁区也得闯。
陈云先向国家粮食部负责人谈了这个问题。粮食部党组经过讨论赞同陈云的意见。决定向中央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并将报告送交分管粮食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又经周恩来请示毛泽东,中央终于同意了陈云的建议。
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表示赞成陈云进口粮食的意见。
第一船进口粮食是从澳大利亚购来的,运到天津新港,时间是1961年2月。离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表态赞同进口粮食仅一个多月时间。1961年2月7日至11日,陈云亲自到天津新港码头视察卸船装车情况及河北省对这批粮食的安排。特别是对如何卸下这一船粮食,他也亲自过问、指导。
要进口粮食就需要外汇,要外汇就得有东西出口,而且还要压缩别的东西进口。为此,陈云又亲自抓外贸出口工作。
当时中国出口换汇主要靠农副土特产品和传统手工业产品。对此,陈云分析说:“现在有进口两百万吨粮食的可能,已经快要签合同了;如果能再多进来一些,我们也要。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有些东西要出口,比如核桃、瓜子、红枣等,国内吃得就少了。我们现在究竟要顾哪一头?我看,要顾进口粮食这一头。如果顾那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是解决不了大问题的,还不如把这些有出口市场的东西都集结起来,换粮食进来。”“总之,顾了东头顾不了西头,要有所得就会有所失。如果这也舍不得丢掉,那也舍不得丢掉,结果什么也得不到就是了。”
为了搞好产品出口,争取进口更多的粮食,陈云作了周到的考虑,提出要建立出口商品基地。“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涮羊肉,张小泉的剪刀,苏州的檀香扇,杭州的绸伞等等,过去都有较固定的原料供应基地,现在我们都打乱平分了,是不符合经济原则的。”他提出要用一年半的时间,把出口商品基地搞起来,以便能稳定出口,争取外汇,增加粮食进口。
由于粮食紧张,造成棉农的棉花生产也下降,致使穿衣也成为国计民生中的重要问题。但当吃饭与穿衣、进口粮食与进口棉花发生矛盾时,陈云坚决把进口粮食放在第一位。当时老百姓的布票已经很少,但陈云说“讨论进口粮食的时候,我们还是定下来每人再减少一尺布,每人减少一尺布,就可以多进口十亿斤粮食……”因为吃饭、穿衣两相比较,吃饭问题更紧要。
确定进口粮食决策后,陈云同周恩来一道,与粮食、外贸等部门负责人一起,多次商量进口粮食数量,并使进口数量逐渐增加。
在那个年代,向哪个国家进口粮食也是有所选择的。美国虽是世界粮食市场的大供应商,但因中美关系尚未解冻,大家都似乎有意回避。只从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订购粮食,而不从美国进口。在1961年8月的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又向毛泽东提出,可否通过当时同中国关系比较密切的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毛泽东表示可以。不久后,美国粮食就通过法国,源源不断地运进了中国。
从1961年到1965年,国家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左右,进口的这些粮食占我国当时粮食总量虽很小,但它在粮食的调度上,作为国家掌握的大宗粮源,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的。
(摘自《读报参考》 唐正芒/文)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财经五人小组组长的陈云果断向中央提议,挤出一部分外汇,从国外进口粮食,以缓解严重粮食危机。吃进口粮在当时是个禁区,因为我国一直在强调自力更生。更何况,自建国以后,我国每年都出口粮食,而今突然说要进口粮食,这在国内外会造成什么影响可想而知。而不进口粮食,饿死人的情况就会更趋严重,造成的政治影响将会更大。所以禁区也得闯。
陈云先向国家粮食部负责人谈了这个问题。粮食部党组经过讨论赞同陈云的意见。决定向中央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并将报告送交分管粮食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又经周恩来请示毛泽东,中央终于同意了陈云的建议。
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表示赞成陈云进口粮食的意见。
第一船进口粮食是从澳大利亚购来的,运到天津新港,时间是1961年2月。离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表态赞同进口粮食仅一个多月时间。1961年2月7日至11日,陈云亲自到天津新港码头视察卸船装车情况及河北省对这批粮食的安排。特别是对如何卸下这一船粮食,他也亲自过问、指导。
要进口粮食就需要外汇,要外汇就得有东西出口,而且还要压缩别的东西进口。为此,陈云又亲自抓外贸出口工作。
当时中国出口换汇主要靠农副土特产品和传统手工业产品。对此,陈云分析说:“现在有进口两百万吨粮食的可能,已经快要签合同了;如果能再多进来一些,我们也要。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有些东西要出口,比如核桃、瓜子、红枣等,国内吃得就少了。我们现在究竟要顾哪一头?我看,要顾进口粮食这一头。如果顾那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是解决不了大问题的,还不如把这些有出口市场的东西都集结起来,换粮食进来。”“总之,顾了东头顾不了西头,要有所得就会有所失。如果这也舍不得丢掉,那也舍不得丢掉,结果什么也得不到就是了。”
为了搞好产品出口,争取进口更多的粮食,陈云作了周到的考虑,提出要建立出口商品基地。“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涮羊肉,张小泉的剪刀,苏州的檀香扇,杭州的绸伞等等,过去都有较固定的原料供应基地,现在我们都打乱平分了,是不符合经济原则的。”他提出要用一年半的时间,把出口商品基地搞起来,以便能稳定出口,争取外汇,增加粮食进口。
由于粮食紧张,造成棉农的棉花生产也下降,致使穿衣也成为国计民生中的重要问题。但当吃饭与穿衣、进口粮食与进口棉花发生矛盾时,陈云坚决把进口粮食放在第一位。当时老百姓的布票已经很少,但陈云说“讨论进口粮食的时候,我们还是定下来每人再减少一尺布,每人减少一尺布,就可以多进口十亿斤粮食……”因为吃饭、穿衣两相比较,吃饭问题更紧要。
确定进口粮食决策后,陈云同周恩来一道,与粮食、外贸等部门负责人一起,多次商量进口粮食数量,并使进口数量逐渐增加。
在那个年代,向哪个国家进口粮食也是有所选择的。美国虽是世界粮食市场的大供应商,但因中美关系尚未解冻,大家都似乎有意回避。只从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订购粮食,而不从美国进口。在1961年8月的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又向毛泽东提出,可否通过当时同中国关系比较密切的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毛泽东表示可以。不久后,美国粮食就通过法国,源源不断地运进了中国。
从1961年到1965年,国家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左右,进口的这些粮食占我国当时粮食总量虽很小,但它在粮食的调度上,作为国家掌握的大宗粮源,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的。
(摘自《读报参考》 唐正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