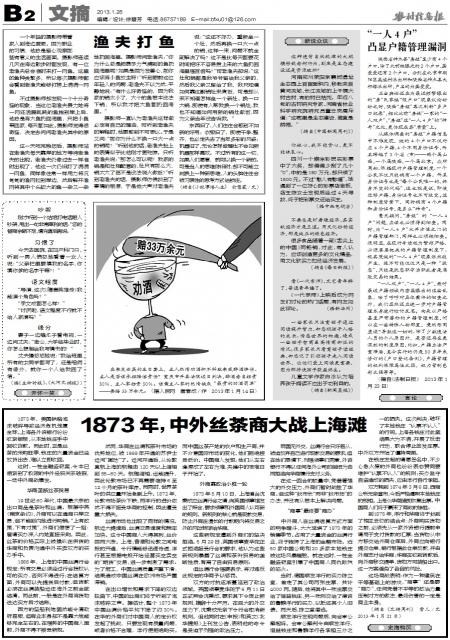1873年,中外丝茶商大战上海滩
1873年,美国铁路泡沫破碎导致经济危机笼罩全球。上海各外资银行纷纷收紧银根,从本地钱庄手中回收贷款。而此时,正是丝茶的采购旺季,钱庄的大量资金已经放贷出去,难以立即收回。
这时,一桩金融盗窃案,令本已绷紧到了极限的中外经贸关系破裂,一场中外商战爆发。
华商垄断丝茶贸易
19世纪60年代,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是茶叶和丝绸。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外商可以在通商口岸交易,但不能到内地进行购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外商们便想了一招:雇请买办深入内地直接采购。因此,丝茶的价格实际上被操纵在供货的华商和负责沟通中外买卖双方的买办手中。
1866年,上海的中国丝绸行会规定:所有交易必须经过行会授权认可的买办,否则不得进行;在结算方面,外商可以先提货后付款,但货款必须在丝绸装船运往海外之前全部结清。而此前,一般是在外商将货物送达买方后才结账。
西方的坚船利炮固然能令清政府屈服,但商业本身却不是靠大炮能够完全左右的。在强势的中国商人面前,外商不得不接受新规。
然而,华商在丝绸和茶叶市场的优势地位,被1869年开通的苏伊士运河“撼动”了。运河开通后,从伦敦直航上海的航程由120天以上缩短到55-60天。航程缩短、运能提升,因此伦敦市场已不再需要维持6至12个月的茶叶库存。而同时,世界茶叶的供应量开始急剧上升。1872年,伦敦市场茶价下跌,而洋行的进价依然不得不接受华商的控制,因此遭受重大损失。
丝绸市场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航运大提速后,丝绸交易速度和频率加快。这令中国商人大得其利,丝价因而大涨。上海、香港和伦敦之间电报的开通,令行情能够迅速传递,洋行甚至根据电报开始经营买空卖空的“期货”交易,进一步刺激了需求。为了赶工,中国丝绸质量严重下滑,结果造成中国丝绸在欧洲市场严重滞销。
在出口增长和需求下降的双边扭曲下,中国的丝商们终于听到了泡沫破碎之声。据估计,整个1873年中国丝绸价格平均下降了约30%。在华的外商们对中国商人的定价权发起了挑战,只要发现有质量问题,或者价格不合理,洋行便拒绝购买。而中国丝茶产地的农户和生产商,并不介意国际市场的变化,他们拒绝接受低价。中国商人发现:他们从左右逢源成了左右为难,夹缝中的艰难日子开始了。
外商靠政治小胜一轮
1873年5月10日,上海道台沈秉成应丝绸行会之请,向英国领事馆发出了照会,要求领事和外国商人认可新的规则。新规则的核心就是现款交易,防止外商在漫长的付款期内将交易之外的风险转嫁给华商。
这些新规定遭到外商们的坚决拒绝。5月29日,英国领事麦华陀正式拒绝接受行会的要求,他认为这些新规则暴露了丝绸和茶叶贸易的垄断性质,背离了自由贸易原则。
但丝绸行会强硬表示,将对违反此规定的华商予以惩罚。
双方的对抗逐渐蔓延到了政治领域。英国领事麦华陀于6月11日正式照会沈秉成,要求其下令废止新规则,措辞十分严厉。在巨大的外交压力下,沈秉成无奈下令行会取消新规则。但他同时在《申报》和英文《北华捷报》上刊发公告,表明他的命令是受迫于列强的政治压力。
弱国无外交,丝绸行会只好屈从,被迫放弃自己进行现款交易的要求。但在他们恳请下,列强领事们同意,外资银行不得以任何海外公司的倒闭为由而拒绝向华商履行支付义务。
在这一回合的较量中,凭借着强大的外交压力,外商们暂时战胜了华商。但这种“找市长”而非“找市场”的办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商事”最终要“商办”
中外商人在丝绸结算方式方面的明争暗斗,大大延误了1873年的销售季节。占用了大量资金的丝绸行业,终于拖垮了上海的金融市场。近50家中国公司和20多家本地钱庄被这场风暴摧毁。就在这时,一桩金融盗窃案引爆了中国商人同仇敌忾的怒火。
当时,德国顺发洋行的买办陈立堂,偷走了其公司两张庄票,共计4000两。随后,他将其中一张庄票交给了恒益钱庄,另一张则交给了德资的鲁麟洋行的买办,以抵还其个人旧债。两天后,陈立堂潜逃。
顺发洋行发现问题后,向会审公廨起诉。会审公廨判令由顺发洋行、恒益钱庄和鲁麟洋行各承担三分之
一的损失。这次判决,破坏
了本地钱庄“认票不认人”
的行规。上海各钱庄对此案
结果大为不满,开展了反击
行动,联合停止签发庄票。中外双方开始了僵持局面。
在钱庄发起的请愿签名中,不少心急火燎的外商也纷纷表态赞同要维护“认票不认人”的规则;买办监守自盗造成的损失,应由洋行自行承担。
双方耗到1874年3月6日,西商公所无奈宣布,今后严格遵照本地钱庄的规矩。上海众华商随即恢复出票。中国商人们终于赢来了商战的惨胜。
到1875年,洋行和华商终于找到了相互妥协的结合点:外商购买货物之前,必须先从一家外资银行提前申请用于支付货款的汇票;当货物从中方移交给外商仓库后,外商应向银行提交仓单,银行根据此仓单放款,并由外商支付给华商;华商在收到货款后,向外商移交提单,货物方可装船出口。这一方案避免了各自的风险。
这场商战表明:作为一种建筑在平等基础上的游戏,“商事”还是要“商办”,任何凭借不平等的政治力量压制对方的做法,最终伤害的一定是商业本身。
(摘自《文摘周刊》 雪儿/文2013年1月21日)
这时,一桩金融盗窃案,令本已绷紧到了极限的中外经贸关系破裂,一场中外商战爆发。
华商垄断丝茶贸易
19世纪60年代,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是茶叶和丝绸。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外商可以在通商口岸交易,但不能到内地进行购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外商们便想了一招:雇请买办深入内地直接采购。因此,丝茶的价格实际上被操纵在供货的华商和负责沟通中外买卖双方的买办手中。
1866年,上海的中国丝绸行会规定:所有交易必须经过行会授权认可的买办,否则不得进行;在结算方面,外商可以先提货后付款,但货款必须在丝绸装船运往海外之前全部结清。而此前,一般是在外商将货物送达买方后才结账。
西方的坚船利炮固然能令清政府屈服,但商业本身却不是靠大炮能够完全左右的。在强势的中国商人面前,外商不得不接受新规。
然而,华商在丝绸和茶叶市场的优势地位,被1869年开通的苏伊士运河“撼动”了。运河开通后,从伦敦直航上海的航程由120天以上缩短到55-60天。航程缩短、运能提升,因此伦敦市场已不再需要维持6至12个月的茶叶库存。而同时,世界茶叶的供应量开始急剧上升。1872年,伦敦市场茶价下跌,而洋行的进价依然不得不接受华商的控制,因此遭受重大损失。
丝绸市场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航运大提速后,丝绸交易速度和频率加快。这令中国商人大得其利,丝价因而大涨。上海、香港和伦敦之间电报的开通,令行情能够迅速传递,洋行甚至根据电报开始经营买空卖空的“期货”交易,进一步刺激了需求。为了赶工,中国丝绸质量严重下滑,结果造成中国丝绸在欧洲市场严重滞销。
在出口增长和需求下降的双边扭曲下,中国的丝商们终于听到了泡沫破碎之声。据估计,整个1873年中国丝绸价格平均下降了约30%。在华的外商们对中国商人的定价权发起了挑战,只要发现有质量问题,或者价格不合理,洋行便拒绝购买。而中国丝茶产地的农户和生产商,并不介意国际市场的变化,他们拒绝接受低价。中国商人发现:他们从左右逢源成了左右为难,夹缝中的艰难日子开始了。
外商靠政治小胜一轮
1873年5月10日,上海道台沈秉成应丝绸行会之请,向英国领事馆发出了照会,要求领事和外国商人认可新的规则。新规则的核心就是现款交易,防止外商在漫长的付款期内将交易之外的风险转嫁给华商。
这些新规定遭到外商们的坚决拒绝。5月29日,英国领事麦华陀正式拒绝接受行会的要求,他认为这些新规则暴露了丝绸和茶叶贸易的垄断性质,背离了自由贸易原则。
但丝绸行会强硬表示,将对违反此规定的华商予以惩罚。
双方的对抗逐渐蔓延到了政治领域。英国领事麦华陀于6月11日正式照会沈秉成,要求其下令废止新规则,措辞十分严厉。在巨大的外交压力下,沈秉成无奈下令行会取消新规则。但他同时在《申报》和英文《北华捷报》上刊发公告,表明他的命令是受迫于列强的政治压力。
弱国无外交,丝绸行会只好屈从,被迫放弃自己进行现款交易的要求。但在他们恳请下,列强领事们同意,外资银行不得以任何海外公司的倒闭为由而拒绝向华商履行支付义务。
在这一回合的较量中,凭借着强大的外交压力,外商们暂时战胜了华商。但这种“找市长”而非“找市场”的办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商事”最终要“商办”
中外商人在丝绸结算方式方面的明争暗斗,大大延误了1873年的销售季节。占用了大量资金的丝绸行业,终于拖垮了上海的金融市场。近50家中国公司和20多家本地钱庄被这场风暴摧毁。就在这时,一桩金融盗窃案引爆了中国商人同仇敌忾的怒火。
当时,德国顺发洋行的买办陈立堂,偷走了其公司两张庄票,共计4000两。随后,他将其中一张庄票交给了恒益钱庄,另一张则交给了德资的鲁麟洋行的买办,以抵还其个人旧债。两天后,陈立堂潜逃。
顺发洋行发现问题后,向会审公廨起诉。会审公廨判令由顺发洋行、恒益钱庄和鲁麟洋行各承担三分之
一的损失。这次判决,破坏
了本地钱庄“认票不认人”
的行规。上海各钱庄对此案
结果大为不满,开展了反击
行动,联合停止签发庄票。中外双方开始了僵持局面。
在钱庄发起的请愿签名中,不少心急火燎的外商也纷纷表态赞同要维护“认票不认人”的规则;买办监守自盗造成的损失,应由洋行自行承担。
双方耗到1874年3月6日,西商公所无奈宣布,今后严格遵照本地钱庄的规矩。上海众华商随即恢复出票。中国商人们终于赢来了商战的惨胜。
到1875年,洋行和华商终于找到了相互妥协的结合点:外商购买货物之前,必须先从一家外资银行提前申请用于支付货款的汇票;当货物从中方移交给外商仓库后,外商应向银行提交仓单,银行根据此仓单放款,并由外商支付给华商;华商在收到货款后,向外商移交提单,货物方可装船出口。这一方案避免了各自的风险。
这场商战表明:作为一种建筑在平等基础上的游戏,“商事”还是要“商办”,任何凭借不平等的政治力量压制对方的做法,最终伤害的一定是商业本身。
(摘自《文摘周刊》 雪儿/文2013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