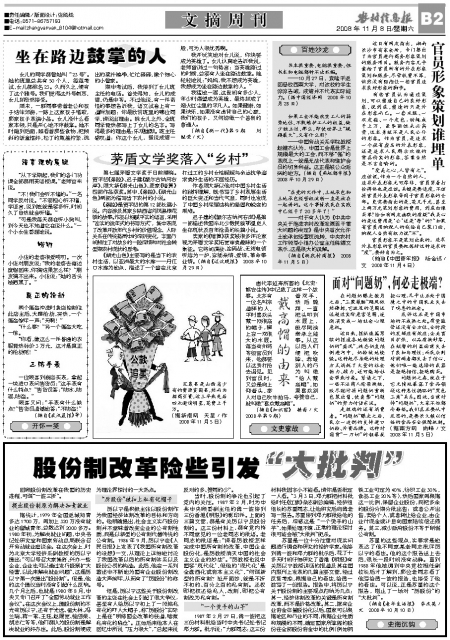股份制改革险些引发“大批判”
回顾股份制改革在我国的历史进程,可谓“一波三折”。
提出股份制原为解决知青就业
据统计,1979年全国返城知青多达1700万,再加上320万没有就业的留城青年,总数达到2000多万。1980年初,为解决就业问题,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劳动就业座谈会。在这次会上,时为北京大学经济系副教授的厉以宁提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这是厉以宁第一次提出“股份制”。但是,他的这个提议当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几个月之后,也就是1980年8月,中央又专门召开了“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提股份制的不光有厉以宁,还有于光远、童大林、冯兰瑞、蒋一苇、王珏、赵履宽、鲍恩荣、胡志仁等等,他们都认为股份制是解决就业的好办法。此后,股份制便成为理论界探讨的一大热点。
“厉股份”被扣上私有化帽子
厉以宁是积极主张以股份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的。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实行股份制并不意味着改变企业的公有制性质,而是以新型的公有制代替传统的公有制。1986年9月,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从理论上详细地讨论了我国改革以后的所有制体系以及股份公司的构造。此后,他在一系列著述中不断地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大声疾呼,从而有了“厉股份”的称号。
但是,厉以宁这些关于股份制改革的主张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争议,甚至有人给厉以宁扣上了一顶搞私有化的吓人大帽子,称“厉股份”实际上是在“明修国企改革的栈道,暗渡私有化的陈仓”。正如后来他本人在回忆中所说“压力很大”,“总起来说反对的多、赞同的少”。
当时,股份制的争论也引起了党内的关注。1987年2月,时为中共中央顾委副主任的薄一波接到三份香港《明报》的影印件。上面的三篇文章,都是有关厉以宁及股份制的。这三份材料上,都有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一位老同志的批语。老同志的批语是:“请看厉教授怎样完成中国所有制的改革,中国企业股份化,是厉教授消灭中国的社会主义企业的妙法”。“厉教授也说中国要‘现代化’,但他的‘现代化’是全盘西化或资本主义化”,“何谓新型的所有制?扯开面纱,就是不折不扣的、百分之百的私有制。还权即把权还给私人,改制,即把公有制改为私有制。”
“一个烫手的山芋”
1987年2月27日,薄一波把这三份材料批给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批示说:“力群同志:这三份材料我因字小不能看。请你是否批定一人看。”3月3日,邓力群把材料批给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经济组组长的苏星同志,让他研究后向薄老写一报告。苏星接到邓力群批给他的任务后,深感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如果处理不慎,正常的理论探讨很可能会被“大批判”扼杀。
苏星是一位十分注重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的经济学家。他接到薄一波和邓力群的批示后,花了十多天时间仔细研究了香港《明报》有关厉以宁教授讲话的报道及其在国内报刊上发表的几篇主要文章,经过反复考虑,根据自己的看法,给薄一波写了一份报告。报告中,将厉以宁关于股份制的主要观点归纳为几点:其一,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所有制改革,而不是价格改革。其二,原有企业资金存量股份化以后,国家可以根据地区和行业的不同,根据企业性质和规模的不同,确定国家所掌握的股份在全部股份资金中的比例(例如钢铁工业可定为40%,纺织工业30%,食品工业20%等),然后国家再根据这一比例,保留企业股份,而把多余的股份分期分批出售:或者公开出售,卖给个人,或者转让给企业,由企业付现金或计息向国家陆续偿还债务。其三,减少政府股份不等于削弱公有制。
苏星的这些观点,实事求是地表达了他不同意某老同志批评厉以宁的看法。他的这个报告送上去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动静。直到1988年他被调到中央党校担任副校长后才了解到,那位老同志看了他写给薄一波的报告,也接受了他的看法。可以说,正是苏星的这个报告,阻止了一场对“厉股份”的“大批判”。
(摘自《老年生活报》 李庆英/文 2008年10月10日)
提出股份制原为解决知青就业
据统计,1979年全国返城知青多达1700万,再加上320万没有就业的留城青年,总数达到2000多万。1980年初,为解决就业问题,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劳动就业座谈会。在这次会上,时为北京大学经济系副教授的厉以宁提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这是厉以宁第一次提出“股份制”。但是,他的这个提议当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几个月之后,也就是1980年8月,中央又专门召开了“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提股份制的不光有厉以宁,还有于光远、童大林、冯兰瑞、蒋一苇、王珏、赵履宽、鲍恩荣、胡志仁等等,他们都认为股份制是解决就业的好办法。此后,股份制便成为理论界探讨的一大热点。
“厉股份”被扣上私有化帽子
厉以宁是积极主张以股份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的。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实行股份制并不意味着改变企业的公有制性质,而是以新型的公有制代替传统的公有制。1986年9月,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从理论上详细地讨论了我国改革以后的所有制体系以及股份公司的构造。此后,他在一系列著述中不断地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大声疾呼,从而有了“厉股份”的称号。
但是,厉以宁这些关于股份制改革的主张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争议,甚至有人给厉以宁扣上了一顶搞私有化的吓人大帽子,称“厉股份”实际上是在“明修国企改革的栈道,暗渡私有化的陈仓”。正如后来他本人在回忆中所说“压力很大”,“总起来说反对的多、赞同的少”。
当时,股份制的争论也引起了党内的关注。1987年2月,时为中共中央顾委副主任的薄一波接到三份香港《明报》的影印件。上面的三篇文章,都是有关厉以宁及股份制的。这三份材料上,都有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一位老同志的批语。老同志的批语是:“请看厉教授怎样完成中国所有制的改革,中国企业股份化,是厉教授消灭中国的社会主义企业的妙法”。“厉教授也说中国要‘现代化’,但他的‘现代化’是全盘西化或资本主义化”,“何谓新型的所有制?扯开面纱,就是不折不扣的、百分之百的私有制。还权即把权还给私人,改制,即把公有制改为私有制。”
“一个烫手的山芋”
1987年2月27日,薄一波把这三份材料批给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批示说:“力群同志:这三份材料我因字小不能看。请你是否批定一人看。”3月3日,邓力群把材料批给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经济组组长的苏星同志,让他研究后向薄老写一报告。苏星接到邓力群批给他的任务后,深感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如果处理不慎,正常的理论探讨很可能会被“大批判”扼杀。
苏星是一位十分注重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的经济学家。他接到薄一波和邓力群的批示后,花了十多天时间仔细研究了香港《明报》有关厉以宁教授讲话的报道及其在国内报刊上发表的几篇主要文章,经过反复考虑,根据自己的看法,给薄一波写了一份报告。报告中,将厉以宁关于股份制的主要观点归纳为几点:其一,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所有制改革,而不是价格改革。其二,原有企业资金存量股份化以后,国家可以根据地区和行业的不同,根据企业性质和规模的不同,确定国家所掌握的股份在全部股份资金中的比例(例如钢铁工业可定为40%,纺织工业30%,食品工业20%等),然后国家再根据这一比例,保留企业股份,而把多余的股份分期分批出售:或者公开出售,卖给个人,或者转让给企业,由企业付现金或计息向国家陆续偿还债务。其三,减少政府股份不等于削弱公有制。
苏星的这些观点,实事求是地表达了他不同意某老同志批评厉以宁的看法。他的这个报告送上去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动静。直到1988年他被调到中央党校担任副校长后才了解到,那位老同志看了他写给薄一波的报告,也接受了他的看法。可以说,正是苏星的这个报告,阻止了一场对“厉股份”的“大批判”。
(摘自《老年生活报》 李庆英/文 2008年10月10日)